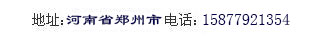上述史记中已能证明摔跤在忻州民众间代代流传,是与边关频繁的战事直接相关。到了元代,雁门关一代数千年的战乱才逐渐趋于安定,原因是元朝是蒙古人南侵中原后建立的大元帝国,其北方的边境疆域辽阔宽广,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蒙古高原,这里又成了大元帝国的内陆区域,入主中元的蒙古贵族在这里跑马圈地,广建牧场,同时也带来了游牧人擅长的摔跤、骑马、射箭等传统习俗,其中游牧人的摔跤与当地人的角抵相融相汇后形成的民间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大元王朝在对华夏的统治维持了不足百年的光景后便被朱元璋所建的明王朝所取代,明王朝建立之初,由于战乱之因,这里和全国许多地方赤地千里,人烟稀少,因此明王朝几代统治者决定从内地向这里和许多无人区大举移民,移民到此的内地人,带来了中原人的庙会文化,他们在自己移居到此的村乡纷纷建立自己信奉的寺庙和神堂,并确定各自的庙会时间和仪式,烧香许愿、求神拜佛、祈佑平安,于是在明朝大移民后的忻州境内就出现了“村村有寺庙、巷巷有神堂”现象,那么有寺庙就有庙会、有庙会就有祭祀活动。
在我国古代庙会文化的民俗活动中,“酬神演戏”是大家通用的,另有什么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活动也要加入“酬神演戏”的庙祀行列,那就各显其有了。在这个时期,忻州有数千年传统活动的“角抵”斗胜项目,便顺理成章地加入到了庙会活动的行列当中去了。明清时期的忻州大大小小的庙会一年不下数百次,仅崞县一地(今原平市)一年当中就有“四大庙会八小会,七十二个渺渺会”流传,有时一个祭祀某位神灵的庙会活动一天就有好几个村庄同时进行,那么就有同样的“酬神演戏”和“角抵”斗胜都参与其中。提供唱戏的戏班子是相对有组织的专业团体,而参与“角抵”斗胜的众多跤手则是民间即兴自发现场组织的零散人员。由于“酬神演戏”既娱神又娱己,故参与“角抵”斗胜的人员更加广泛随意,不论老少青壮本村外村人人均可参加,最终获胜者就可得到祭祀神灵后的“礼牲”活羊一只的奖赏,这便是忻州民间特色摔跤“挠羊赛”形成的原始起因。全国知名的我市文化学者肖黎民先生在其撰写的《跤乡赋》中是这样叙述的:“俗谓挠羊赛者,角抵斗胜之跤种,游牧民族之遗风,实雄风所展,乃壮士所为,相沿成俗蔚为一方之体育盛事。盖当庙会,斗智斗勇,英雄跌对(及摔跤)地毋分轻重,人毋分老幼,跤手难分难解,斗智斗勇,跤迷通宵达旦,助兴助威,胜者挠举活羊以当祭礼,观者高抬好汉,目为明星,后由酬神演戏的庙祀活动渐演为乡民劳作之余兴。田间地头,常摆赛场,四季阴晴,照打擂台,何妨赤膊上阵,每可顺手牵羊,英雄不问出处,一跤尽显风流”。这个文赋,着实是对跤乡忻州历代开展摔跤群众性、普及性、民间性最贴切的描述。
文章来源:《跤乡跤事》作者:胡竟侖
页面编辑:蔚正华
白癜风治疗有效的药物最好白癜风医院电话